图书BOOKS
接通的意义
- 作 者:项阳
- 出版日期:2014-12-01
- 出 版 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 ISBN:978-7-5059-9034-0
- 价 格:65元
在线购买
收 藏
图书详情
本书简介
本书是作者新世纪以来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学术思考与感悟,涉及学术理念与方法论,诸如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接通”以及从多种功能意义上对中国音乐文化整体性认知,非仅是审美与欣赏的意义;在对历史上王朝典章制度深入挖掘梳理形成整体学术理念的前提下辨析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下活态,认知在乐籍制度下由官属乐人承载的诸多音声技艺类型的生发、演化,乐籍制度解体后乡间社会对历史音乐文化大传统的接衍与积淀,对当下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和地方性乐种的艺术性本体存在以及多功能为用进行综合辨析,意在构建由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贯穿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系列新学术理念、方法与观点期待与学界分享。
作者简介
项阳,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硕博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学术著作有《中国弓弦乐器史》、《山西乐户研究》、《乐户: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日本大阪2007)、《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合著);论文集《当传统遭遇现代》、《以乐观礼》等。独立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课题,有较为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国际音乐节评委(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1997),中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专家评审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文化部职称评审专家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艺科)评委,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目录
理念认知
003/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
024/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
048/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
065/音乐文化的功能性与主导脉络一致性下的区域特色
069/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080/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
087/“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论纲
103/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
112/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
接通历史
125/堕民,在底边社会中创造和承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138/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
159/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
176/—本元代乐籍佼佼者的传书——关于夏庭芝的《青楼集》
191/男唱女声:乐籍制度解体之后的特殊现象——由榆林小曲引发的相关思考
205/从官养到民养/腔种间的博弈——乐籍制度解体后戏曲的区域、地方性选择
225/雍、乾禁乐籍与女伶:中国戏曲发展的分水岭
历史的田野
249/当下非主流化生存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形式——以鲁西南和冀中为例
266/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
278/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与践行者
290/黎锦晖:时代弄潮与世纪悲情
302/岱庙、东岳庙会用乐的相关问题
316/关于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323/后记
序言
以历史人类学方法论来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是多年前我在硕士与博士阶段学习经历为“中国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理论”,前者侧重文献,后者注重活态;一是读书期间能够有针对性地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研究生毕业后乔建中所长力主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并给我下达《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编纂的任务,使得我能够走向“历史的田野”,而且下去了就不想离开。得益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这20余载一直都在从事与学术相关的工作,围绕着几个选题不断深入,方有点滴收获。
来到音乐研究所,我从《中国弓弦乐器史》的研究入手,进而从事山西省音乐文物的收集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历史上为官属乐人的乐户后人群体,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逐渐感知历史上乐户群体是制度下生存在籍的国家专业乐人,由此引发对乐籍制度的探求。以乐籍制度下乐人承载为把握,认知凡官方创承并所用的礼乐和俗乐形态多属这个群体所为,他们是国家制度下体系内服务于社会的专业乐人群体。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乐籍制度被雍正禁除,遍布全国县衙以上官府为用的专业乐人们以其承载的种种音声技艺、作品和谙熟的礼制仪式转而服务于民间,完成了服务对象的转型并使得“官乐”积淀在民间成为可能。以上认知多是在对乐户后人及其承载实地考察过程中,将历史文献与当下乐人活态对接所生发,形成学术理念之后进而梳理国家制度层面历经千余载形成传统之后对当下的实际影响,通过对这个群体全方位辨析,探究这个群体存在及其承载的诸种功能性意义,试图改变学界既有宫廷与民间二元论之认知(所谓宫廷有制度,民间松散无序)我们所依循的实际上是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方法。
历史人类学是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理念与方法论相结合用于相关学术研究对象。历史学更多侧重文献解读和辨析;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外来的学科方法论,侧重文化的活态研究,注重人类在当下诸种行为方式的把握。两种学科有着各自论域,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不注重历史,如此产生局限。学术界将这两种学科理念有效结合,可在两种学科理念既有论域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从而发既往之未发,或称是在建立史学理念的基础上侧重文化活态的整体把握。
我在厦门大学读研期间对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有所认知,因此在实地考察中能够运用这种学术理念。本来从事音乐史学研究,因实地考察传统音乐活态就有了两种学科理念结合之机缘,原本只是朦胧的使用,接触到“历史的民族音乐学”(音乐学界的称谓,实际上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用于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继而把握历史人类学学科“原点”的意义,结合研究对这种学术理念有着深度认同。在下以为,历史人类学“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概念,前者代表了既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而后者则显现历史观念,在对传统活态进行把握与辨析的过程中回溯,从历史文献学乃至多种相关学科意义上梳理传统的逻辑起点以及衍化脉络。既然研究对象是“传统”,一定是在历史上生成,活态传承到当下。基于这种认知,我们便可以在对活态把握的前提下去探讨与传统千丝万缕之关联。
我来到音乐研究所之后所做都需实地考察,因而生发出了几个相关课题,与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结合最为紧密的当属《山西乐户研究》,继而是《中国乐籍制度研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以乐观礼》,以及《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几个课题都有这种学术方法论的支撑,也可以说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感悟,并自觉而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
在音乐学界,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是两个学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学起步较晚,是在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音乐史学影响所建。换言之,中国音乐史学更多借鉴了欧洲专业音乐发展史为参照系,注重音乐艺术。在这样的学术观照下,历经几代学者近百年的努力,使得中国音乐史学形成了当下论域和面貌。我们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前辈学者怀有极大的敬意,毕竟我们有了属于中国的音乐史学。
西方或称欧洲音乐史面对的是欧洲各国引领潮流的专业音乐层面,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以审美与欣赏为主旨的、注重音乐流派与发展、关注音乐家与作品的撰史方式。以此为参照,中国人亦可写出一本结构类似、内容不同的音乐史。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否该仅仅是这种艺术的意义,以西方专业音乐史的理念来撰中国音乐文化史能否将全部的内涵以为把握,缺失的是什么呢?依在下看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显然有自己的轨迹,这是中国人对音乐认知与使用的样态,因此在撰写中国音乐史时,的确应该首先去考虑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其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究竟有怎样的功用,与社会群体、个人究竟有怎样的关联,除审美与欣赏之外还应把握怎样的意义,音乐在多种为用的意义上是否限于一时,还是长久的以类分意义一以贯之?恰恰是基于以上的思考,当我们对中国历史文献加以梳理时方能够感受到既有中国音乐史学尚有一些研究领域缺失,或称是某种忽略,诸如对礼乐贯穿性内涵的把握,礼乐与俗乐各有怎样的用途,乐籍制度对中国音乐文化有怎样的功用,这种制度何以形成又何以被禁除,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怎样的多功能性、多类型性意义,何以说既有音乐史学对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意义把握不足?我们说,学术是要发展的,也只有当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方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认知,只有跳将出来方能够感悟既有之不足,从而拓展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领域,朝着更接近历史原貌的方向去努力。
从多种教材可以看出,学界对传统音乐的活态多以民间音乐加以认知。传统的活体在当下的确是民间态,如此将中国历史大传统中积淀在当下的活态以民间音乐认知也并无不妥。然而,如果是将这种理念与宫廷、宗教、文人等联系在一起使用,则显示出学界还是有整体意识的,所谓宫廷对应民间,这就是说除了宫廷就是民间的意义,这样的认知显然还是有一定的缺失。
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梳理清楚,就会看到这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在乐籍体系下是由国家制度下的官属乐人所创承的,雍正禁除乐籍,这些官属乐人承载的多种音声技艺形式和形式下的作品便随同这个群体更多转而积淀在民间,所以说,当下在民间的传统音乐形态应该有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即民间所有不断的新创造;一是历史上国家意义的音乐形态积淀在民间者,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这个层面的音声技艺形式及其承载的作品其实是“很不民间”的样态。所以说,仅仅以民间音乐加以认知和界定,显然难以整体把握其内涵与深层意义。
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以上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展开。我们更多把握的是音乐文化史的意义,要研究音乐文化史,就不能够仅仅将目光定位在艺术的层面。换言之,这音乐既是艺术更是文化的有机构成。探讨音乐文化的发展则要涉及更为宽广的层次与层面,要调整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借助于多学科的学术理念来认知与音乐文化相关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接通”的意义。
所谓接通,就是要在充分认知音乐的多种功能性意义的基础上(还是拓展的意义,不能仅从艺术的视角)从与音乐文化相关的多层面加以考量,接通之后就会出现与既往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新面貌,关键在于学术理念的调整。曾有学者讲到:我们知道学术界有这种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但民间所承载的“大传统”在哪里呢?没有啊!是的,如果不是建立起这种接通的理念,如果不是真正走向“历史的田野”或称回到历史现场去把握曾经的“国家在场”,如果不是真正深入下去找到相关的路径的确是很难体味,但这显然不是拒绝从民间认知传统之所在的理由。我们说,接受这种学术理念是要有勇气的,毕竟许多研究者所接受的学术理念已经固化,接受新理念需要调整,这本来就有一种自我挑战的意义。
这是一本文集,在下以为还是有一定的系统性。也希望能够给音乐学界把握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一种新视角。
项阳
2013年10月17日
相关推荐
畅销排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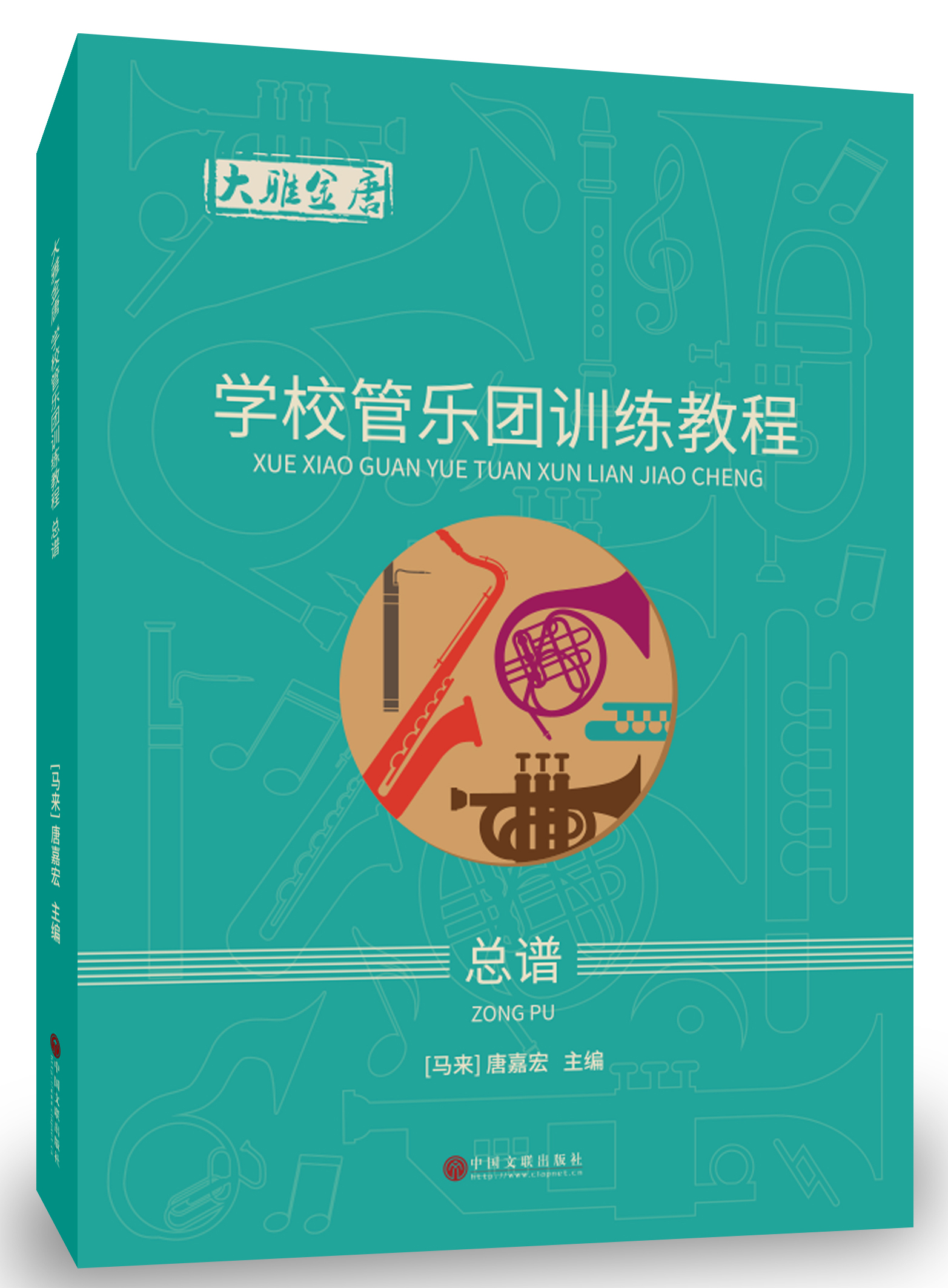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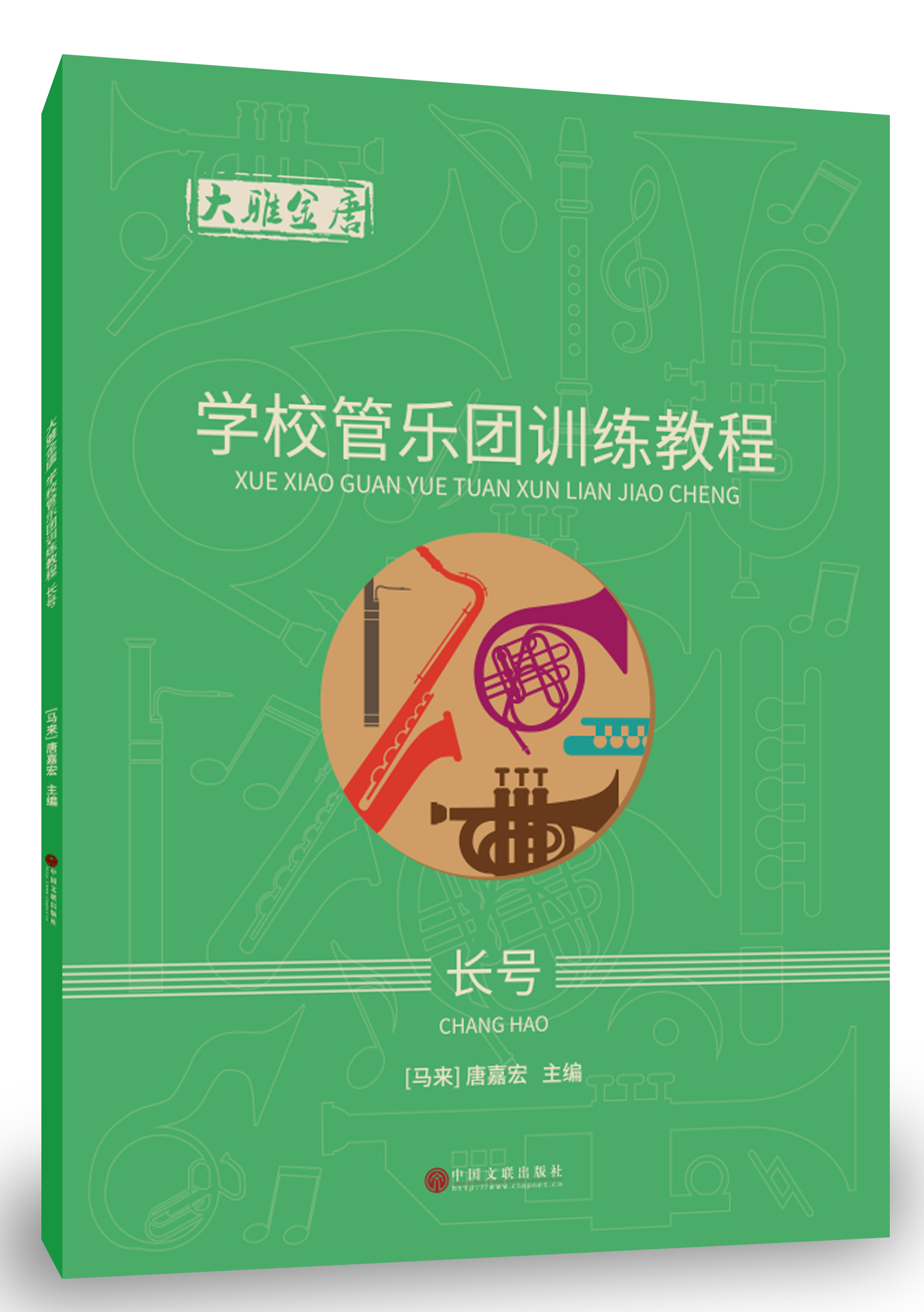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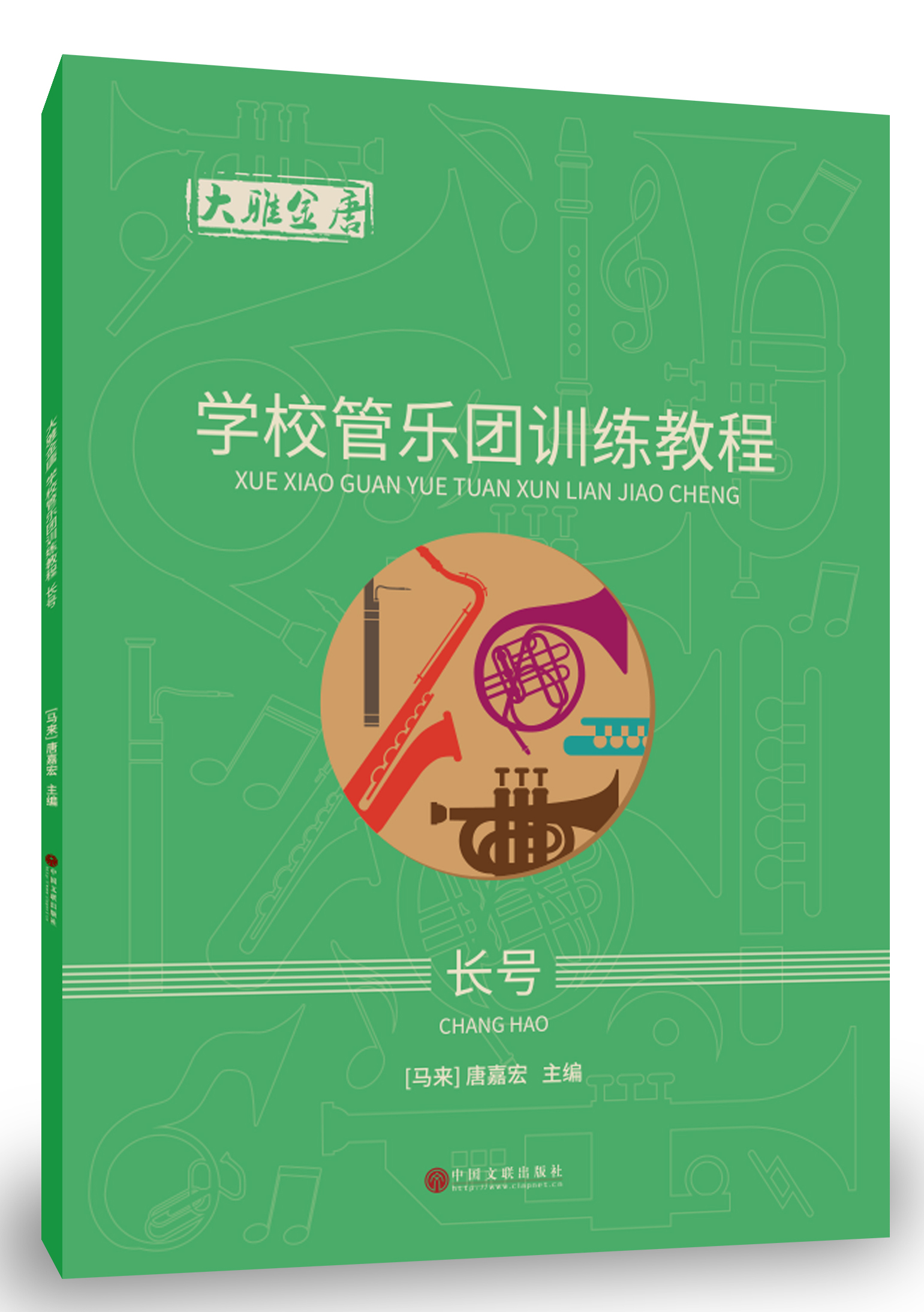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最新资讯
-
努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 全国文艺界...
2022/10/18 -
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2022/06/21 -
推动新时代文艺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
2022/03/02 -
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度工作表彰大会暨202...
2022/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