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术
- 作 者:邓福星
- 出版日期:2014-12-01
- 出 版 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 ISBN:978-7-5059-9035-7
- 价 格:71元
本书简介
该书是作者学术探索的精华,遴选自1980年以来作者撰写的多部著作。重点探讨艺术发生学问题、艺术抽象化问题、中国美术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问题、中西美术观念比较问题等,相关论述具有独创性和科学性,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是同步发生的观点,新颖独特,具有开创意义。
003/艺术前的艺术
073/中国原始素陶研究
111/艺术发生探讨方法与途径
第二辑 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
121/绘画的抽象性
149/抽象绘画语言特征及其价值
第三辑 中西美术观念比较
179/中西美术自然观念比较
209/中西美术宗教观念比较
第四辑 论20世纪中国美术
235/20世纪中国画转型论纲
245/中国美术论辩百年回首
第五辑 王朝闻美学思想研究
257/王朝闻美学思想述评
283/王朝闻美学思想的理论个性——再读《王朝闻集》
第六辑 画梅研究
297/梅谭
代后记
362/治学33年回顾
治学33年回顾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美术界对“抽象美”“形式与内容”“自我表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但限于认识,讨论难得深入。这是我把《绘画的抽象性》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缘起。写这篇论文没有感到艰难,回想起来,当是得益于在部队做宣传干事讲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随后在天津工艺美院从事美术创作的经历,从而有过抽象思维的训练和绘画创作的体会。在完成4万字论文后,还不到答辩时间,就又翻译了《油画色彩教程》,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中英文版先后发表,得到王瑶先生、周振甫先生的赞赏。刘刚纪先生认为我的硕士论文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成为我后来主要的研究方法。
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对史前艺术的研究,之所以确定这一选题,缘于当时一个相关的课题。1983年,王朝闻先生作为学术牵头人承担了15卷本(后改为12卷)《中国美术史》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我参加了该项目试点卷《原始卷》的编写工作。于是,“作揖搔脚背”,我把博士论文的写作同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查阅资料,一方面到全国重要史前遗址、考古所、博物馆考察拍摄。近距离接触远古遗存,揣摩、体味、探寻其中的奥秘,还同有关专家交流切磋,从中收益极大。博士论文《原始艺术研究》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实地考察写出来的。论文答辩通过后,以《艺术前的艺术》为书名出版,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有论者认为书中提出的“同步说”补救了一些传统艺术起源理论的偏颇,较为可信。我的这一观点被写进一些“艺术概论”的教科书里。正像论者所说,它最大的价值是在艺术发生学方法论上的突破。此后,我对《原始卷》中“素陶”两章的写作,也是基于对原始遗存的考察,以小见大,力求专、细而具体,解剖麻雀,采用了同博士论文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在2006年写作《梅谭》,对于梅文化及画梅艺术的研究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读研,仅仅是入门,是练兵,是热身。接下来才进入“正话”。
二
我协助朝闻先生主持的另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是14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项目集中了国内有关专家研究、撰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民间美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和基本面貌,深入论述了其艺术特征、美学价值、工艺制式和社会功能。该书摆脱了套用一般美术分类的方法而从功能意义上进行分类,并揭示了民间美术的原发性、贴近生活、作者和受众的普遍性及其厚重而恒久的活力。这一项目历经4年完成,在海峡两岸相继出版,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研究院最高学术奖特别成果奖,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等奖。在1999年9月23日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颁奖大会上,我代表课题组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手中接过红彤彤的奖状。
上述两个课题基本上属于美术史研究及侧重史料的学科建设,出于对长期以来比较滞后的美术理论研究的推进和学科建设的考虑,我相继策划、组织编写了《美术学文库》《中国民间美术基础理论丛书》《当代艺术美学文选》等多卷本丛书。
十几年间,我先后主编了十几部美术史论研究丛书。
参加集体项目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层面对同一题目分析、阐释,和而不同,相互之间碰撞、切磋、互补,这无疑是一种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当然也要求、迫使牵头人或主持者必须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的前瞻性,以便对研究课题的全局把握,以学术见识和包容性把分散的成果融为一体。
三
我认为,美术研究所作为唯一的国家级美术研究机构,在研究美术历史及理论的同时,应该密切地关注美术创作现状、美术思潮,使科研工作贴近当代美术实践,积极参与美术界重大活动。1989年4月11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新文人画展”开幕式上,我致辞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新文人画展”是绘画史上的第一次,以美术研究所的名义主办画展也是首开先河。此后,美研所开始频频为画家举办各种规模的美术展览,从个展、联展、专题展,到全国性的“油画双年展”和国际性的“世界华人书画展”等等。美研所举办研讨会接连不断,包括美术家作品研讨、学术交流研讨、全国乃至国际性的专题研讨。美研所不仅参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美术史论研究生,而且于1992年开办书画高研班,为当今春笋般涌现的书画进修班开了先例。美研所最早举办了名家作品邀请展,设立并进行了首次全国美术学论文评奖,同国内外美术家及美术史论家建立了广泛联系。美研所当时在促进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美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与此同时,美研所的学术成果(著作和论文)也在全院各所中遥遥领先。我讲述美研所当时学术活跃的蒸蒸气象,不是用以作为自己的学术成就,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所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首先是时代使然。经临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我幸运地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当谋其政,当作其事,我见证也经历了那段中国美术的辉煌。从而,也使我在那段岁月里,学术识见得到提高。
创办《美术观察》杂志社也是一例。199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因经费紧缺,不再供养各所期刊。有些所的刊物因此不得不停办。美研所原来的学术季刊《美术史论》(只是编辑部)难以为继。我认定美研所不能没有一个刊物,无论如何,必须办一个保持学术性而更贴近美术现状的期刊,于是申报、筹办《美术观察》月刊杂志社。创办之艰难不必说了。《美术观察》月刊的诞生其实是转轨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第一次开了学术性美术期刊自负盈亏的先河。编期刊是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也是一定意义的治学,是一种更切实际的学问。《美术观察》的诞生和健康成长增强了我再办一份《美术观察报》的设想。就在朝向这一目标努力之际,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横来,劫难降临,我离开了《美术观察》。
在读研之后的大约15年间,我参加过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评审活动:各类美术作品的入选、评奖,文艺类图书的评奖,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博士后出站的评审,艺术类课题的审核及验收,以及制定全国艺术类研究课题的规划纲要等。如今想来,这些活动虽然耗用了不少时间,但也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就是在这样一段特定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了我匆匆的足迹。李希凡老院长说:“那些年他(指我)忙乎的,一直是美术史项目和所里的工作,自己很少有时间写书和创作。”那些年,经常冒出一些新奇的想法或构想,但终日都在紧张忙乱之中,无暇提笔记录下来,任偶发的思想火花随生随灭。于今每念及此,不免觉得可惜。好在自知不曾虚掷时光,已为学术尽了心力,何况,正是以我如上经历,得以“观千剑而识器”,学术视野大开,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感受能力和认知能力,不同于他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例如,或许由于我对史、论、评都有涉入,从对学科全局的关注,产生了整合的意识,从而提出建立“美术学”学科的设想,撰写了勾画美术整体的《美术概论》;或许由于曾经认真地啃过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就艺术发生学的问题提出了“艺术的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发生”的假说;或许因为办刊和对于当代美术的关注和参与,所以撰写了近200篇美术评论文章;或许由于有美术创作实践的感受,所以写出了《中国原始素陶研究》和《梅谭》一类专门而具体的论文,如此等等。
四
从33岁读研迄今又过去了33个年头。我的治学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最大幸运。不逢这个伟大的时代,就没有我33年治学的经历。我有幸受业王朝闻先生,从读研到主持课题,从学业到经世,受益良多。我还要感谢命运,赐予我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蒙田曾以在光亮下和暗影中譬喻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我以为用“绚烂”和“平淡”喻之更为贴近。后者是前者的复归。铅华洗尽,复归纯正和本真,这是又一种人生境界,虽然平淡,其意趣却醇浓而深厚。经过人生跌宕,自觉比以前成熟了许多,但时而却又感到对学理、对世事、对人生的茫然与不解,自愧无知。记得朝闻先生80多岁时曾经略带诙谐地慨叹:“对艺术,对人生刚有一点感悟,竟到了准备西去的年龄!”现在觉得先生的话并非只是逗趣。回来还说“治学”,其与人生实在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就是学习罢了,不仅学习某一种专业,还要学习做人处事,学习生活和生存。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试题,是一条不知尽头的人生之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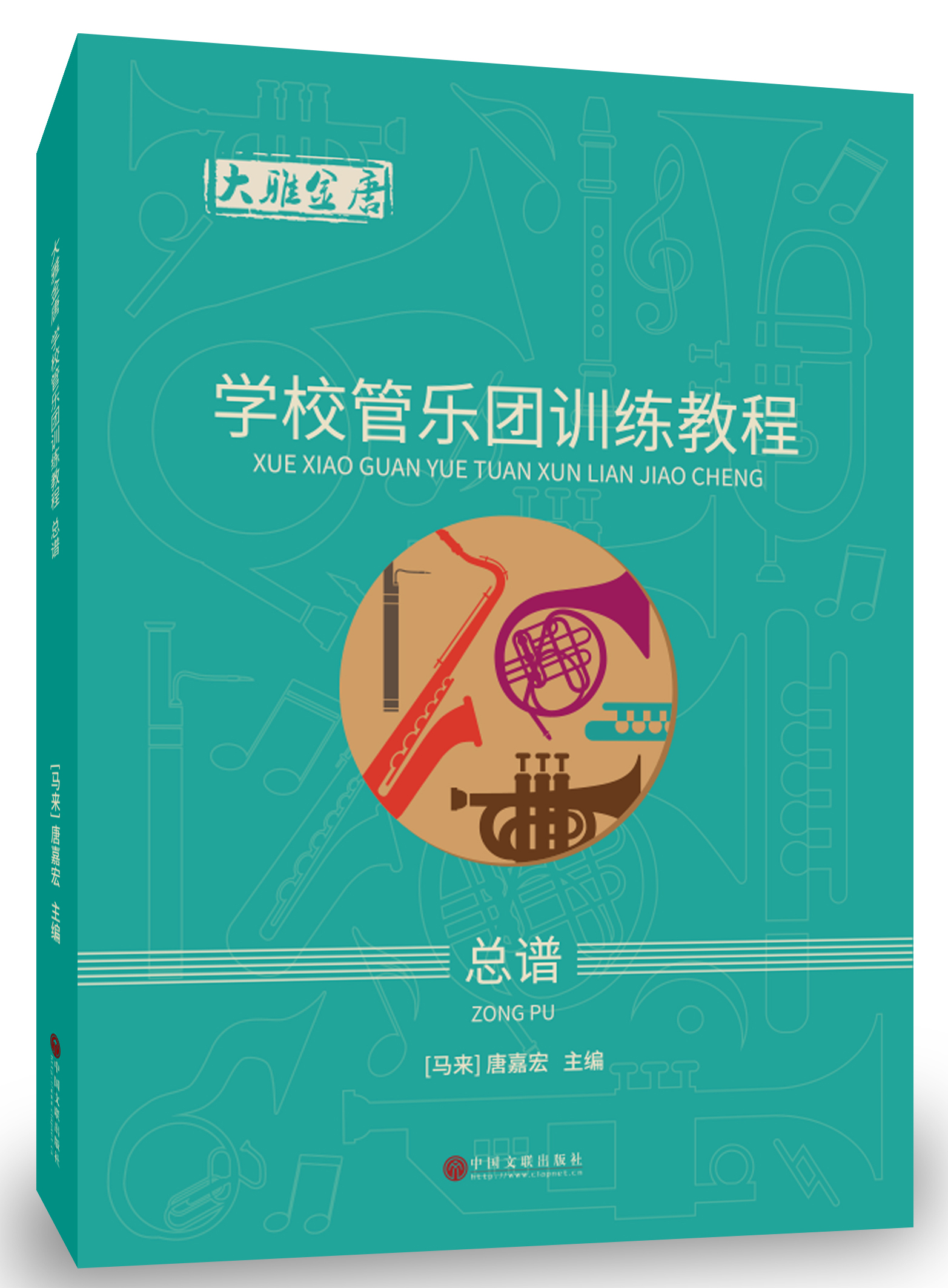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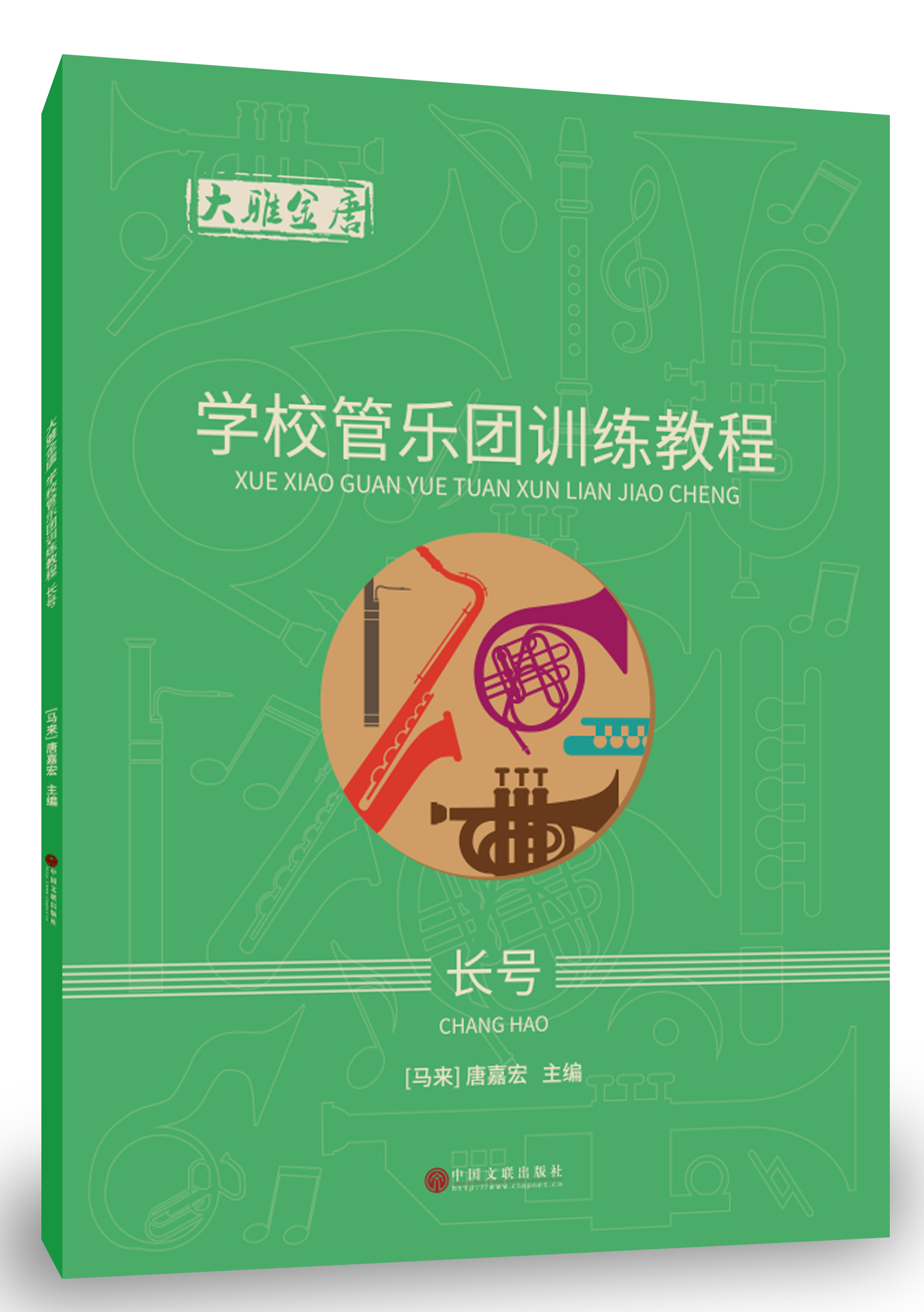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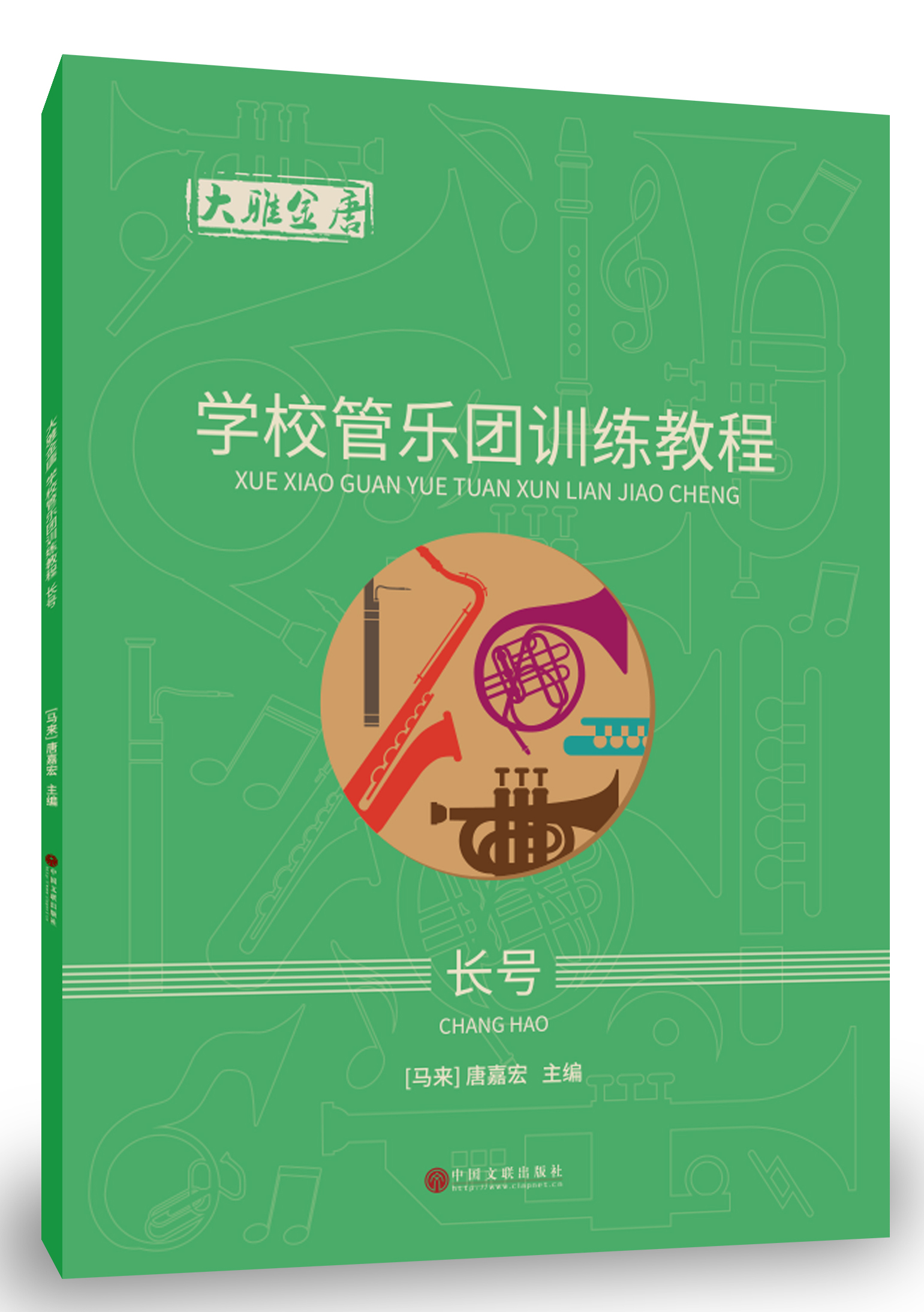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努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 全国文艺界...
2022/10/18 -
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2022/06/21 -
推动新时代文艺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
2022/03/02 -
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度工作表彰大会暨202...
2022/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