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BOOKS
当代文艺理论家如是说
- 作 者:王文革 李明军 熊元义/主编
- 出版日期:2015-04-30
- 出 版 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 ISBN:978-7-5059-9486-7
- 价 格:80元
在线购买
收 藏
图书详情
本书简介
近几年来,《文艺报》陆续采访了活跃在中国当代的权威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即是对这些权威文艺理论家的采访录集萃。这些文艺理论家集老中青于一体,35位左右。有老一辈:陈涌、钱谷融、李希凡、叶朗、胡经之、钱 中文、童庆炳等,也有中青年理论界如:李心峰、王岳川、王一川、李心峰等。这些文艺理论家所谈的问题基本涉及当代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难题等,见解精辟,思想深刻。
目录
001 陈涌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011 钱谷融谈:文艺批评的“奥秘””
024 李希凡谈: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
035 钱中文谈:文艺理论的新理性精神
047 田本相谈:百年中国现代戏剧
059 胡经之谈:诗意的裁判与文艺的价值
072 谭霈生谈:戏剧理论批评与戏剧发展方向
085 吴元迈谈:追求中外文学的共同“文心”
095 王元骧谈:文艺理论的使命与承担
106 陆贵山谈:从宏大视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
118 童庆炳谈: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
131 孙绍振谈: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
143 彭立勋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
155 陈美兰谈:珍惜作家精神劳动的成果
162 叶朗谈:美学要关注人生关注艺术
170 杜书瀛谈:审美与价值
181 何镇邦谈: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学
188 王先霈谈:文艺理论的本土化与时代化
199 董学文谈:建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
209 朱立元谈:当代文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发展
221 冯宪光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30 仲呈祥谈:文艺批评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41 鲁枢元谈:文艺理论研究的超越与跨界
252 郑欣淼谈: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64 陆建德谈:“伟大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276 陈跃红谈:现代中文教育与文学职业理想
288 党圣元谈:重拾民族美学自信
300 王岳川谈:发现东方与再中国化
314 谭好哲谈: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活力
325 余三定谈:文艺批判与文艺创新
336 南帆谈:文学话语的波长
347 陈众议谈:重构当代文艺理论
360 徐放鸣谈:文学的使命与国家形象塑造
372 王杰谈:让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返当代公共话语空间
386 韩永进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400 李心峰谈:艺术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412 王一川谈:自觉应对“艺术学”面临的新挑战
421 熊元义谈:尊重并把握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
439 高玉谈: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
451 后记
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
熊元义 李明军 王文革
中国当代社会正从学习模仿的追赶阶段转向自主创新的创造阶段。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理论创新是先导。然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却出现了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的断档危机。这是很不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为了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我们连续与中老年文艺理论家就当代文艺理论发展问题进行了对话。在与这些文艺理论家的对话中,我们既看到了当代文艺理论的缓慢发展,也发现了不少文艺理论问题。这些文艺理论问题既是当代文艺理论界搁置文艺理论分歧所产生的,也夹杂着一些理论偏见。还有不少当代文艺理论创新看似文艺理论的发展,实则不过是过去的文艺理论重复,只是换了精致的包装而已。因而,只有彻底清除当代文艺理论界日渐弥漫的鄙俗气和清理文艺批评界的含混概念,积极开展文艺理论争鸣,才能真正推动当代文艺理论创新。
清除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鄙俗气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随着文艺理论争鸣的开展日益艰难,不少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史家身上的鄙俗气日趋严重。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一些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史家不是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价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贡献,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史家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甚于追求客观真理,他们既不努力挖掘文艺理论家的独特贡献,也不继续肯定这些文艺理论家在当代文艺发展中仍起积极作用的理论,而是停留在对一些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文艺理论家的评功摆好上。这种鄙俗气严重地制约了这些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史家客观公正地把握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并极大地助长了当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歪风邪气。
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鄙俗气首先表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追求客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这种倾向严重恶化了当代文艺理论的生态环境。
在2014年《江汉论坛》第2期上,我们曾在《理论分歧的搁置与文艺批评的迷失》这篇论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反思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时重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这并无不可。但是,美学家李泽厚却将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民大众追求的是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制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多愁善感的高贵的美。而知识分子工农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这是“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这带来了知识分子“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重新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审美趣味的轮回中,李泽厚鲜明地提出:“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呢?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包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曹雪芹、卡夫卡等等。应该期待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史诗、悲剧,会出现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但是,这又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能两全,如何选择呢?这就要由作家艺术家自己做主了。”而“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文艺的取向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李泽厚尽管承认艺术作品是有价值高下的,即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品高得多,但他却认为文艺的取向是多元的,即“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这又否定了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下判断。李泽厚之所以在美学理论上左右摇摆,难以彻底,就是因为他在迎合中国当代文艺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迷失了方向。李泽厚在文艺批评中不是追求客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消极影响很大,不少文学批评家就是这样在跟着文学现象跑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二是表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积极修正已知的理论错误,而是陶醉在文艺理论的社会影响中。文艺理论家缺乏深刻的反省是很不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提高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响很大的刘再复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不但在哲学和逻辑上存在错误,即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也存在错误,即没有看到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和发展。正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懦夫或者英雄。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
刘再复认为:“在反对斯宾诺莎的机械论时,黑格尔的巨大贡献,正是阐明了这种正确的辩证内容,道破偶然性就是双向可能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正是统一在这种双向可能性的矛盾运动之中。”黑格尔在把握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时提出,凡是偶然的东西,总是既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也具有那样的可能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下)中说:“可能与现实的统一,就是偶然。——偶然的东西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它同时只被规定为可能的,同样有它的他物或对立面。”又说:“偶然的东西,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没有根据;同样也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有一个根据。”刘再复以黑格尔的这些论断为前提提出:“所谓偶然性正是双向可能性。就是说,凡是偶然的东西,总是既有这样的可能性,也有那样的可能性。这种对偶然性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它正是我们打开必然与偶然这对哲学范畴之门的钥匙,也是我们理解二重组合原理哲学基础的关键。”接着,他进一步地指出:“偶然性的真正含义在于双向可能性,也就是说,偶然性包含着可能性的两极,而这两极的最终统一,就是必然性。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的深刻根源就是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矛盾运动,就是这种可能性两极的对立统一运动。在哲学科学里,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差异与同一都是统一序列的概念。在典型塑造中,必然性就是人物性格的共性,偶然性则是人物的个性。必然性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才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偶然性是双向的可能性,即既可能这样又可能那样,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既可能是美的,又可能是丑的,既可能是圣洁的,又可能是鄙俗的,等等。因此,偶然性本身是二极的必然性。这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矛盾,因此,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规定下的双向可能性的统一。就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这就是二重组合原理的哲学根据。”刘再复的这些论断涉及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样三个范畴。对这三个范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分别对它们及其关系作了深刻的把握。
首先,刘再复想当然地认为:“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必然性正是通过双向可能性的矛盾运动才与偶然性构成一对辩证范畴。”这种幻想不但歪曲了黑格尔关于可能性的思想,而且割裂了黑格尔关于必然性的思想。黑格尔明确地指出:“凡认为是可能的,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内容(内容总是具体的)不仅包含不同的规定,而且也包含相反的规定。”但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不能说,凡是可能的因而也是现实的。”这就是说,一个事物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不都是现实的。因为“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这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合,而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发展了的现实性,作为内与外合而为一的更替,作为内与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联合成为一个运动的更替,就是必然性。”黑格尔曾经讥笑“一个人愈是缺乏教育,对于客观事物的特定联系愈是缺乏认识,则他在观察事物时,便愈会驰鹜于各式各样的空洞可能性中。”幻想无限的可能性的刘再复可以说就是黑格尔所讥笑的这种缺乏教育的人。
其次,黑格尔认为:“偶然的事物系指这一事物能存在或不能存在,能这样存在或能那样存在,并指这一事物存在或不存在,这样存在或那样存在,均不取决于自己,而以他物为根据。”刘再复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或”曲解为“和”了。黑格尔关于偶然的事物的思想是丰富的,“或”存在三种现实情形:一是不可同假但可同真,一是一真一假,一是一假一真。而“和”只有一种情形:可以同真。这样,刘再复就阉割了黑格尔丰富的辩证思想。
显然,刘再复对黑格尔关于偶然性的思想的理解是肤浅和错误的。
其实,1987年,在《性格转化论》中,我们就对《性格组合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指出刘再复不仅混淆了可能性与偶然性,把可能性视为偶然性,而且混淆了动机和行为的现实,把动机当作了行为的现
实,典型地表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可以说,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上而已。到了1999年,刘再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再版《性格组合论》时并没有修正这些理论错误,而是陶醉在没被遗忘中。当代文艺理论界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时不是深入地探究这个“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是非,而是侧重肯定它的影响力。这种重视文艺理论影响而轻视文艺理论是非的倾向助长了当代文艺理论界重视怎么说而不关心说什么的倾向。文艺理论界如果不认真甄别所说内容的真假,而只注重怎么说,就会模糊甚至混淆是非、善恶和美丑的界限。
三是表现为文艺理论家在文艺争鸣中不尊重对方,而是自以为是。这种倾向严重影响了文艺理论争鸣的充分开展,极大地阻碍了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
近些年来,我们和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围绕文艺的审美超越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深入而系统地批判后发现文艺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王元骧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仅妨碍广大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而且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这就是说,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既然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作家的主观愿望是如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概括和提升的?难道是自然吻合的?王元骧接着说:“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自然是属于主观的、意识的、精神的东西,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普照光,就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因为事实上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此在”内心的基本形象’,‘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是已经处在形而上学中的’理想不是空想,它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失而为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都是以美的形式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所以鲍桑葵认为‘理想化是艺术的特征’,‘它与其是背离现实的想象的产物,不如说其本身就是终极真实性的生活与神圣的显示’,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体现,它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更真切、更深刻的反映,它形式上是主观的,而实际上是客观的。”这实际上是认为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首先,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很不同的。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开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作家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根本对立。其次,既然在现实世界中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的,那么,这种历史鸿沟是如何填平或化解的?如果作家在审美超越中可以填平或化解这种历史鸿沟,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界就行了。显然,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而已,乃是以更为精致的形式重复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刘再复等人的自由主义文艺理论。这场文艺理论论战虽然并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大文艺理论论战,但却没有引起当代文艺界应有的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当代文艺批评界理论兴趣的丧失。2011年,我们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载于《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中深入而系统地批判了王元骧近些年来在文艺理论上的探索,初步把握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2012年,王元骧在《理论的分歧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载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对我们进行了反批评。这种文艺理论争鸣本来是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但是,王元骧的反批评却既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也没有全面回应我们的质疑,而主要是自我申辩。
在反批评中,王元骧提出了论辩原则,认为在开展文艺争鸣时,文艺理论家如果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思想,抓住彼此之间思想的根本分歧,从根本上把正误是非的道理说透彻了,那么,无需给对方扣上多少帽子,对方的理论也会不攻自破。王元骧提出的论辩原则是我们非常赞同的。可惜的是,王元骧并没有遵循这些论辩原则。在反批评中,王元骧只引用了我们的结论而阉割了这个结论的理论前提,就认为我们全盘继承了“打棍子”、“扣帽子”这种简单粗暴的作风。这种割裂结论和前提的联系的反驳可以说既不能真正解决文艺理论分歧,也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在《理论分歧的解决与文艺批评的深化》(载于《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这篇论文中,我们深入地比较了彼此的理论并鲜明地指出了彼此理论分歧所在。接着,在《文艺批评家的气度》(载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王元骧在文艺争鸣中不仅缺乏文艺理论家的气度,而且不够尊重对方,没有真正把握对方在理论上的发展,而是割裂对方理论前提和结论的联系,以自我证明代替对对方的逐层驳斥。王元骧的这种自我申辩既无助于文艺理论争鸣的充分开展,也无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
四是表现为文艺理论家在梳理和总结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时不是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而是阉割历史。这极大地挫伤了当代文艺理论家的创造心理。
中国当代社会实行改革开放30年后,文艺理论发展在新世纪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对于这段即将谢幕的文艺理论发展,文艺理论界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近些年来,文艺理论界相继有人对这段时期文艺理论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2006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教材编写丛书”的形式隆重推出的文艺理论家朱立元主编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既凝结了这些年来文艺理论界对这段时期文艺理论发展总结和反思的成果,也凸显了文艺理论界反思和总结这段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不同立场。这个《调查报告》既是童庆炳主持的一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的子课题最终成果,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2004年,这个《调查报告》还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可见,这个《调查报告》是经过不少文艺理论权威专家论证和多次讨论后才出版的。所以,我们批评这个《调查报告》所存在的严重不足和根本缺陷就不是针对极个别人。也就是说,这个《调查报告》所暴露的问题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这个《调查报告》在对不少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把握上可以说是既很不客观,也很不全面。譬如,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研究部分,这个《调查报告》只是分别列举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倾向即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理论体系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理论体系。但是,它没有全面考察这些倾向的源流、先后和主次,只是平行地罗列了一些文艺理论专家的认识。这就很不客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较早涉及这个文艺理论问题的是陆默林。陆默林提出这个文艺理论问题主要不是针对文艺界一些人的片面认识,主要是针对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的糊涂思想。1978年底,陆默林在第一次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上应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发言,较为系统地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并指出:我们过去没有提出和探讨过这个问题,在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遗产上,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和阐发工作,深化我们的认识。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号上的《体系和精神》一文就是陆默林在这个发言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此文随后分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一集)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二书。此后,陆默林又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一、二)和《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美学思想》等文中继续探讨了这个文艺理论问题。至于中国文艺理论界有人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断简残章”,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事情。这当然遭到广大正直的文艺理论家的抵制和批判。《调查报告》不仅没有客观地梳理这个发展过程,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展史,而且对抵制和批判“断简残篇”说的各种思想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没有严格区分。这样,《调查报告》所提及的各种思想没有任何逻辑顺序,有些则是因人设事。这种对前人的劳动成果极不尊重严重地干扰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秩序,很不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
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鄙俗气严重地妨碍了当代文艺理论争鸣的充分开展和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科学解决。其实,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发展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当代文艺理论界只有正视并解决这种文艺理论分歧,才有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有序发展。毛泽东在倡导百家争鸣时尖锐地指出:“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有意压抑,只是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不少文艺理论家不敢正视并解决文艺理论分歧,而是搁置这些文艺理论分歧,甚至打压和排斥那些挑战既有秩序的新生力量,以至于出现了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的断档危机。
清理当代文艺批评的含混概念
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出现了“告别理论”的倾向。有些文艺批评家虽然没有公开拒绝文艺理论,但却对文艺理论相当忽视。有些文艺批评家对文艺理论即使在口头上重视,但在实际上却是基本上不重视。有些文艺批评家以为加强文艺批评,就是增加文艺批评的数量。这是本末倒置的。这不仅是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而且充分暴露了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危机。有些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之所以难以透彻,是因为他们理论不彻底,提出并推销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因此,当代文艺批评界只有彻底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才会有精准的文艺批评。
生命写作与历史正气
本来,文学应为历史存正气。但是,不少当代作家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平衡发展中却没有自觉抵制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是躲避崇高,自我矮化。有的文学批评家在诊断中国当代文学的弊病时不是严格区分弘扬正气的文学与宣泄戾气的文学,而是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这些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这显然没有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害。作家的才能虽然有高低大小,但只要他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是生命的投入和耗损,就是灵魂的炼狱和提升,就不能不说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判断没有深入区分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好与坏、高尚与卑下,而是提倡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些空洞的概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界定艺术活动,认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俄国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批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认为艺术不“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这一点也是不对的。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在这种补充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还修正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任何情感都有一个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而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文学表达的对象。普列汉诺夫在把握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认为:“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那些只重视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地指出:“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说:‘问问你自己,任何一种能把你深深控制住的感情,是否都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是否都能够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使他激动?如果能够,那么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如果它不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或者它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那就是卑下的感情’。”因此,普列汉诺夫对艺术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作了两个深刻的规定:一是一个艺术家要看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艺术作品没有思想内容是不行的。但是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损害。”二是艺术要表现正确的思想,“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要是被错误的思想所鼓舞,那他一定会损害自己的作品。”而“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普列汉诺夫的这种文学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文学思想的发展。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这篇战斗檄文中不但指出了当时存在两种文学,而且区分了这两种文学的内在质地和价值高下。这就是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在这个社会中,一种新锐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决到外部来,但是,
它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所压迫,它找不到出路,结果就导致苦闷、忧郁、冷漠。只有单单在文学中,尽管有鞑靼式的审查,还保留有生命和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原故。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在我们这里早就使肩章上的金银线和五光十色的制服黯然失色。”别林斯基热情地肯定了进步文学,坚决地否定了那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与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的反动文学。1846年12月,作家果戈理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一方面否定了他以前所写的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认为那些文学作品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与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别林斯基并没有丝毫的姑息,而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一个曾经通过他奇妙的艺术的和深刻的真实的创作强大有力地促进俄罗斯的自觉,让俄罗斯有机会像在镜子里一样,看到了自己的伟大作家现在却带着这本书出现,他在这本书中为了基督和教会教导野蛮的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的愤怒吗?”别林斯基认为不管怎么样,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绝不会成功,不久就将被人遗忘。显然,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被人忘却绝不是缺少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而是思想反动、灵魂卑下。而当代文学批评家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则是历史倒退。因此,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绝不能躲避崇高,自我矮化,而是与中国当代社会这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世代相适应,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先进行列,勇立潮头唱大风,成就文学的高峰。
底层文学与人民文学
在人类文学史上,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绝不局限于反映某一社会阶层,而是在深刻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尽可能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然而,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些文学批评家却不是深刻把握整个历史运动,而是热衷于抢占山头,甚至画地为牢。“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就是这些文学批评家抢占山头的产物。
21世纪初,我们提出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向是有感于中国当代文坛所有最有活力、最有才华和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几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种现象。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向既不是要求广大作家只写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生活,也不是要求广大作家肢解中国当代社会。而“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却狭隘地划定创作范围,既肢解了中国当代社会,也限制了广大作家的视野。首先,社会底层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就不完全是社会底层人民自己造成的。作家如果仅从社会底层人民身上寻找原因,就不可能深刻把握这种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的历史根源。那些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优秀作家不仅写了自己艰辛劳作时的汗水,写了自己孤独绝望时的泪珠,写了工友遭遇不幸时的愤懑,而且写了他们在争取自身权力时与邪恶势力的斗争,是不可能完全局限于社会底层生活的。下岗工人诗人王学忠在《石头下的芽》这首诗中就既深情地讴歌了压在石头下的芽不妥协不屈服的抗争行为,也愤怒地谴责了压迫嫩芽的石头的淫威与卑鄙。“压吧,用你全部的淫威与卑鄙/但千万不要露出一丝缝隙/否则,那颗不屈的头颅/便会在鲜血淋漓里呼吸//呼吸,只要生命还在/抗争便不会停息/风雨雷电中、继续/生我的叶、长我的枝……”石头下的嫩芽的弯曲和变形绝不是自身基因的变异,而是压在身上的石头的压迫和扭曲。这就是说,作家如果不把社会底层生活置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把握,就不可能透彻地反映社会底层生活。其次,文学批评家可以提倡广大作家反映社会底层生活。但是,广大作家却不能局限于这种社会底层生活,而是应从这种社会底层生活出发,又超越这种社会底层生活。作家只有既有入,又有出,才能真正创作出深刻的文学作品,才能达到高远的艺术境界。
有些文学批评家在把握中国当代底层文学时不仅没有看到底层文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以局部代替整体,在底层文学与人民文学之间画上等号。这是相当错误的。21世纪初期,诗人王学忠的身份曾引发文学批评界的一次争论。王学忠是一位下岗工人,写出了不少反映下岗工人在沉重生活中挣扎的诗。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他是工人诗人,有的文学批评家则认为他是工人阶级诗人。这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从职业上识别诗人,后者是从思想上界定诗人。其实,王学忠是工人诗人,还是工人阶级诗人?文学批评界不能仅从职业上判断。王学忠的诗虽然集中反映了被抛弃在社会生活边缘的当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运,但却没有揭示整个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这些被抛弃在社会生活边缘的工人不是当代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当代工人阶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这个整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境遇:有的下岗,有的在岗;不同的人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有的在国营企业,有的在合资企业,有的甚至在私营企业。当代工人阶级因为工作环境和地位的不同,境遇就各不相同,他们对生活的具体感受也就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化,有的仍然是主人,有的却转化为雇佣工人。这种历史的巨变不仅造成工人阶级的每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很不相同,而且造成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无法沟通、理解和支持。这就造成了不少当代工人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使命缺乏充分的理论觉悟。王学忠作为一位下岗工人,不仅饱受了现实生活的艰辛、苦涩、痛苦,而且比较真切地表现了这种具体的感受。但是,这种具体的感受还不是整个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深切感受。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王学忠是近年来从下岗工人中出现的诗人。他的不少诗相当真实地描写了众多下岗工人的悲惨命运及底层人民的生活。可以说,王学忠是一个中国当代诗坛崛起的工人阶级的诗人,至少他已经向这个目标大步迈进了。这是不确切的。如果文学批评界认为那些描写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的诗人是工人阶级诗人,那么,这是将一部分人当作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了。因而,王学忠不是工人阶级诗人,而是工人诗人。有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在工人诗人与工人阶级诗人之间画上等号,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底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因而将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
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是知识分子,都已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处在不断分化重组中。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活力所在。有些文学批评家看不到这种巨大变化,仍以那些固定模式框定这种巨大变化,是徒劳的。这些文学批评家在肯定诗人王学忠时犯了这种错误,在肯定艺术家赵本山时仍犯了这种错误。有些肯定小品《不差钱》的文学批评家则认为,赵本山——刘老根——“二人转”代表的是农民文化、民间文化和外省文化。而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赵本山通过与“毕老爷”的来往吐露了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的“二人转”艺人攀登“主流文艺”与“上流社会”的辛苦,他们感谢上流社会的“八辈祖宗”,绝对听毕老爷的话。赵本山不但代表中国八九亿农民发出了宣言和吼声即我们农民要上“春晚”,我们农民要上北京忽悠城里人,而且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这种肯定批评混淆了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人与农民阶级的区别。真正的农民文化革命是那些维护和捍卫农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和满足他们的根本需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那些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人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些跻身上流社会的个人往往可能最后背叛农民。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在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和徒弟小沈阳、毛毛(丫蛋)所演的农民角色只是会唱歌,想唱歌,而不是倾力唱反映农民命运的歌,倾力唱吐露农民心声的歌。因此,他们跻身上流社会除了个人命运的改变以外,根本看不到中国当代农民命运的丝毫改变。这哪里有农民文化革命的一丝影子? 其实,赵本山和徒弟小沈阳、毛毛(丫蛋)本身就是地道的农民。随着他们在演艺圈走红,他们的命运的确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过上了非常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的命运却依然故我,哪怕是引起社会的一丝关注都没有。显然,这种认为赵本山掀起了农民文化革命的文艺批评不过是将局部等同于整体,混淆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因而不可能真正准确地把握艺术作品。
生理快感与心理美感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深刻认识到单纯感官娱乐并不等于精神快乐这个美学的基本道理。正如有的文学批评家所指出的,有
些作家没有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而是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生活、渲染人的原始本能、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从世界美学史上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恶劣倾向不过是德国诗人、戏剧家和美学家席勒所批判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沉滓泛起。
18世纪末期,席勒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德国艺术的一些不良现象,认为许多德国小说和悲剧仅仅引起眼泪流干和感官情欲的轻快,而精神却成为
空空洞洞的,人的高尚力量全然不由此变得强大;那些流行音乐更是只有令人愉快的搔痒的东西,而没有吸引人、强烈感动人和提高人的东西。也就是说,感官在尽情享受,但是人的精神或自由的原则却成为感性印象的强制的牺牲品。接着,席勒对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在艺术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把握。在《论激情》这篇论文中,席勒特别反对艺术单纯表现情绪激动,认为“情绪激动,作为情绪激动,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表现它,单从它来看,不会有任何美学价值;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没有什么仅仅与感性本性相联系的东西是值得表现的。”而“激情的东西,只有在它是崇高的东西时才是美学的。但是,那仅仅来自感性源泉和仅仅以感觉能力的激发状态为基础的活动,从来就不是崇高的,无论它显示出多大的力量,因为一切崇高的东西仅仅来源于理性。”这就是说,感官上的欢娱不是优美的艺术的欢娱,而能唤起感官喜悦的技能永远不能成为艺术,“只有在这种感性印象按照一种艺术计划来安排、加强或者节制,而这种合计划性又通过表象被我们所认识的时候,才能成为艺术。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能成为自由快感的对象的那些感性印象才会是属于艺术的。也就是说,只是使我们的知性快乐的、安排好的审美趣味,才会是属于艺术的,而不是肉体刺激本身,这种刺激仅仅使我们的感性欢快。”在这个基础上,席勒区分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席勒指出:“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叫做庸俗的表现,相反的表现叫做高尚的表现。”然而,有些中国当代作家却并不执着于艺术的高尚的表现,而是热衷于庸俗的表现。有的文学批评家曾尖锐地批判作家贾平凹的消极写作,认为在贾平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关于性景恋和性畸异的叙写,都是游离的,可有可无的,都显得渲染过度,既不雅,又不美,反映出作家追求生理快感的非审美倾向。这种过度的性景恋和性畸异叙写是一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文学病象。其实,这种文学病象不仅贾平凹有,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还形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潮流。这就是不少文学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现象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一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的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的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这些文学作品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恶俗笑料和噱头,甚至脱离历史胡编乱造,肆意歪曲历史。这些恶俗笑料和噱头除了单纯的感官刺激以外,没有任何社会思想内容。有些恶俗笑料和噱头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满足和迎合人的心灵的那个低贱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部分。眩惑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期文学批评家王国维在引进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时提出来的。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眩惑这个概念就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媚美概念。19世纪早期,叔本华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媚美,一种是积极的媚美,还有一种消极的媚美。这种消极的媚美比积极的媚美更糟,那就是令人作呕的东西。叔本华认为在艺术领域里的媚美既没有美学价值,也不配称为艺术。显然,那些仅以眩惑诱惑人心的中国当代作家严重违背了美的规律。
不过,有的文学批评家虽然准确地看到了贾平凹的小说存在的病态现象,但却没有深入把握这种病态现象产生的根源。贾平凹等作家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生活、渲染人的原始本能、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绝不仅是贾平凹等作家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而是他们没有在沉重生活中深入地开掘出真美,不能上升到更高的阶段,仅能以眩惑诱惑人心。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明确地指出,感性的美虽然是最原始最基本而且最普遍的因素,但却不是效果的最大或主要的因素。美学家蔡仪在深刻把握快感与美感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快感只是美感的阶梯,快感在美感心理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我们并不否认快感在美感中的作用,我们承认快感可以作为美感的阶梯,例如:过强的光线刺目,过弱的光线费眼,过高的声音和不协和的噪音震耳欲聋,都会使感官不快,也不能产生美感。但美感毕竟不能归结为快感,因为美不能完全属于单纯的现象(除部分现象美外)而美感也不能全都停留在感性阶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感固然以快感为重要条件和感性基础,但快感在美感心理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贾平凹等作家由于在审美理想上发生了蜕变,所以不能开掘沉重生活中的真善美,没有从感性的美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即不能以真美感动人,就只能以眩惑诱惑人心。
2014年11月13日
相关推荐
畅销排行
-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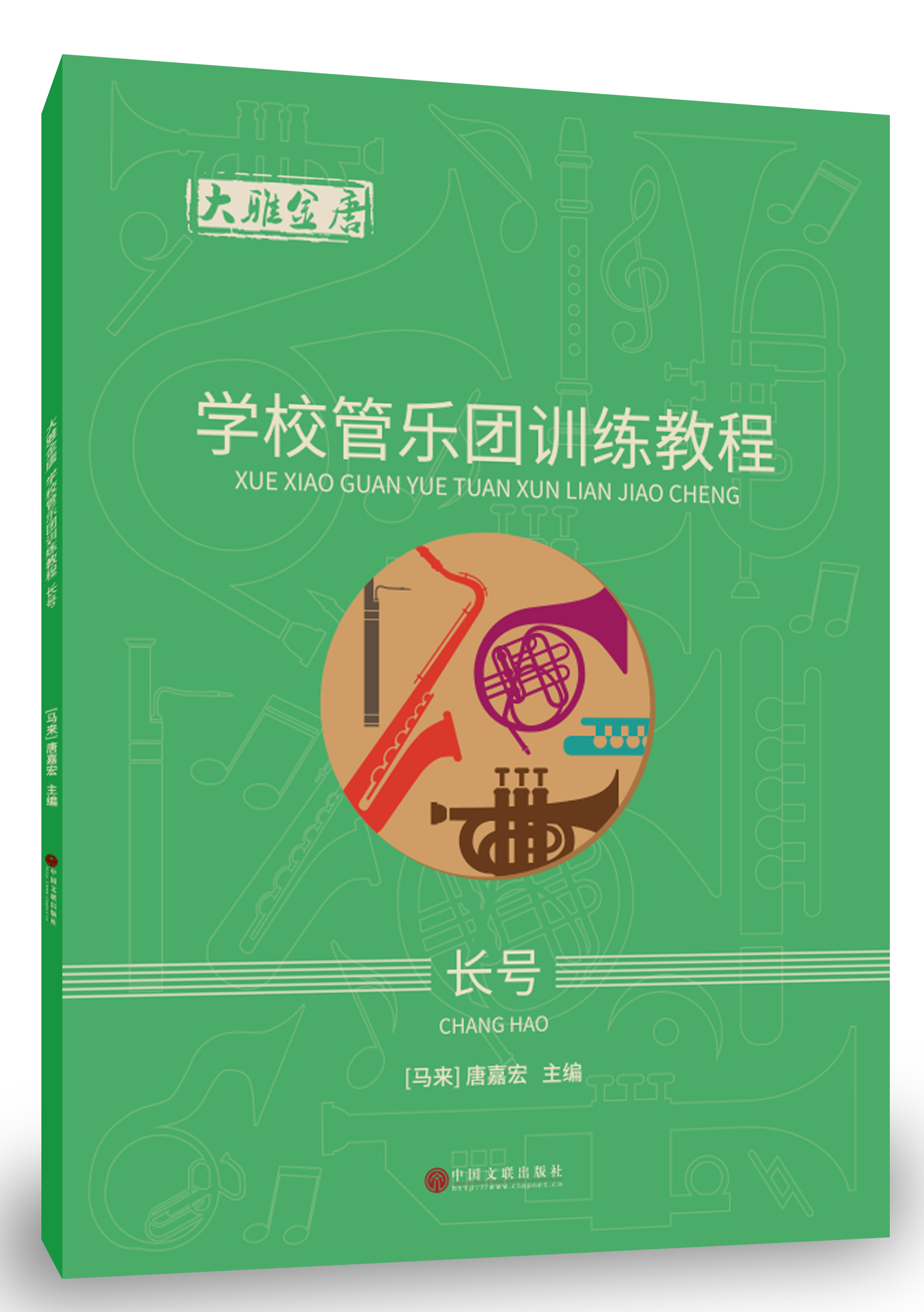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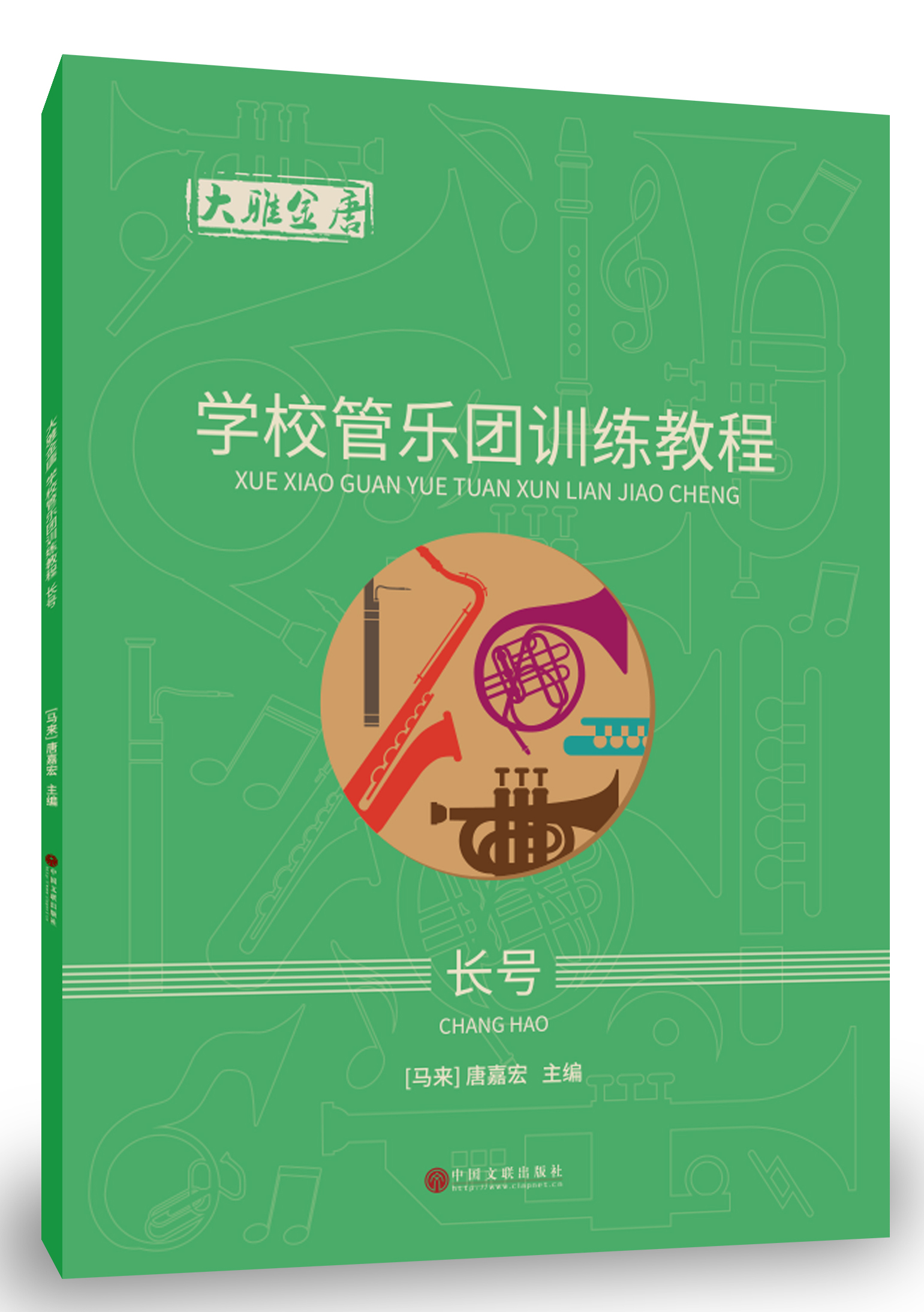
-
学校管乐团训练教...
作者:唐嘉宏简介:
最新资讯
-
努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 全国文艺界...
2022/10/18 -
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2022/06/21 -
推动新时代文艺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
2022/03/02 -
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度工作表彰大会暨202...
2022/02/23








